天馬彩繒 光華博望
——絲綢之路與漢代文明略談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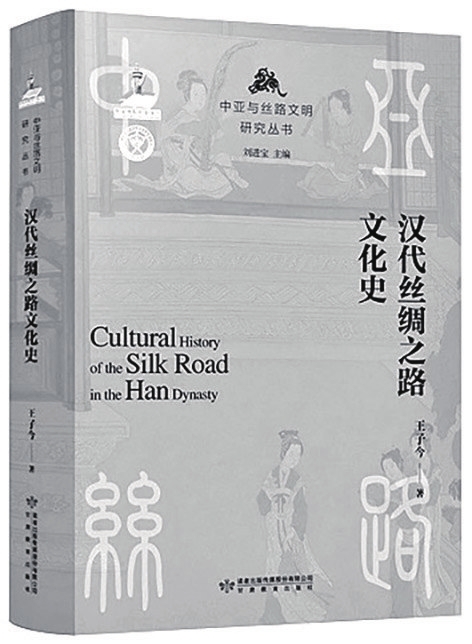
《漢代絲綢之路文化史》 王子今 著 甘肅教育出版社
后世稱作“絲綢之路”的東西文化交流通道,其實(shí)早在張騫誕生之前的年代,就已發(fā)揮便利文化交往的歷史作用了。在漢武帝執(zhí)政時(shí)期,司馬遷記述的“張騫鑿空”(《史記·大宛列傳》),則進(jìn)一步實(shí)現(xiàn)了世界史進(jìn)程中的重大進(jìn)步。經(jīng)由絲路的東西往來,漢文化愈發(fā)成熟與定型。筆者似可得出一個(gè)結(jié)論——倘若沒有絲綢之路,漢代文明可能不會(huì)呈現(xiàn)出當(dāng)前我們所看到的風(fēng)貌。
拙著《漢代絲綢之路文化史》,試圖分四個(gè)部分說明筆者從文化史視角考察漢代絲綢之路的心得。其一為漢代絲綢之路的民族文化交往;其二為漢代絲綢之路的物質(zhì)文化交流;其三為漢代絲綢之路的精神文化交融;其四為漢代絲綢之路的文化史料叢考。通過絲綢之路實(shí)現(xiàn)的文化聯(lián)系,讓漢代文明空前繁榮。
一
據(jù)《漢書》所述,作為漢代絲綢之路重要路段的河西交通,有東西方向“通西域”、南北方向“鬲絕南羌、匈奴”的作用。“胡羌”之外,更有“西域三十六國”,可知這一交通方向民族關(guān)系復(fù)雜。
匈奴是威脅絲路交通安全的強(qiáng)勢(shì)力量。但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《漢書·匈奴傳上》等篇章記載,匈奴“好漢繒絮”,意即匈奴喜好漢地織品,甚至在雙方正式進(jìn)入戰(zhàn)爭(zhēng)狀態(tài)之后,“尚樂關(guān)市,嗜漢財(cái)物,漢亦尚關(guān)市不絕以中之”。“關(guān)市”,是漢與匈奴進(jìn)行貿(mào)易的主要場(chǎng)所。可見,考察漢與匈奴的關(guān)系,不僅可以看到血火刀兵,也能通過絲綢絢麗的色澤和輕柔的質(zhì)感,感受經(jīng)濟(jì)交流史與文化融合史平緩親和的一面。
在絲綢之路上,羌人同樣表現(xiàn)出交通方面的機(jī)動(dòng)性。絲綢之路從河西通向蜀地的線路,有羌人交通開發(fā)的基礎(chǔ)。而西漢名將趙充國與羌人的戰(zhàn)與和,為絲綢之路的交通安全提供了保障。絲綢之路河西路段在民族關(guān)系中的作用,從隔絕羌胡到通貨羌胡,發(fā)生了歷史性轉(zhuǎn)變。民族淵源不很明確的“商胡”“賈胡”“酒家胡”在內(nèi)地的活躍,成為引人注目的漢代文化風(fēng)景。正如陳連慶在《漢唐之際的西域賈胡》一文中所述:“在中西交通開通之后,西域賈胡迅即登場(chǎng)。”東漢時(shí)期,長安仍有人數(shù)可觀的“西域賈胡”。《太平御覽》卷二六四引《東觀漢記》記述京兆功曹楊正的故事,涉及漢光武帝劉秀去世后長安“西域賈胡”的活動(dòng):“楊正為京兆功曹,光武崩,京兆尹出,西域賈胡共起帷帳設(shè)祭。”京兆尹乘車經(jīng)過祭祀場(chǎng)地,“胡牽車令拜”,京兆尹疑惑,“止車”。可見長安地方東漢初年“西域賈胡”數(shù)量相當(dāng)集中,在特殊情況下聚集起來,竟使得地方高級(jí)行政長官一時(shí)難以決斷如何處理這一活動(dòng)。
如上所述,西漢時(shí)期,“西域賈胡”這一群體已在長安積聚了相當(dāng)可觀的力量。這說明,絲綢之路的繁榮促成了新的民族關(guān)系的產(chǎn)生,為后來中國北方的民族大融合開辟了先路。
二
對(duì)于漢代絲綢之路的物質(zhì)文化交流,就織品而言,以往多重視絲綢的西輸。而東來的毛織品,其實(shí)也影響了中原社會(huì)生活。《史記·貨殖列傳》里說,“旃席千具”“比千金之家”。“胡氈”的普及,影響了中原社會(huì)家居物用的形式。
傳說張騫通西域之后傳入中土地方的物種,除“騾驢馲駞,銜尾入塞”(《鹽鐵論·力耕》)之外,主要是有經(jīng)濟(jì)意義的植物。石榴即其中之一,以至于清人俞樾在《曲園雜纂》卷四四《十二月花神議》中,將張騫尊奉為“榴花之神”,體現(xiàn)了民間文化對(duì)相關(guān)歷史現(xiàn)象的記憶。
“酒”是一種在古代中國便已廣泛普及的消費(fèi)品。在對(duì)外交流史中,有“蒲陶酒”的發(fā)現(xiàn)與“蒲陶宮”的營造等跡象,也有“挏馬酒”的引入。另一方面,草原關(guān)市的“酒”“糵”貿(mào)易以及“漢所輸匈奴”的“米糵”(《史記·匈奴列傳》),也值得注意。
關(guān)于“西方”“北胡”“殊域”異色鹽產(chǎn)的文字記錄,體現(xiàn)了中原人對(duì)較為寬廣的空間的經(jīng)濟(jì)地理認(rèn)知,也反映了他們的交通理念與世界意識(shí)。這些知識(shí)的獲得,與絲綢之路交通與文化交流有直接的關(guān)系。其早期記錄,往往可追溯到漢代甚至漢代以前。
三
論及漢代文化,李學(xué)勤等歷史界學(xué)者曾以“輝煌”來形容。“輝煌的漢代文化”,其構(gòu)成包含外來文明的元素。
《續(xù)漢書·五行志一》記載:“靈帝好胡服、胡帳、胡床、胡坐、胡飯、胡空侯、胡笛、胡舞,京都貴戚皆競(jìng)為之。”外族音樂舞蹈的傳入,以及來自更遙遠(yuǎn)地方的“幻人”的表演(《后漢書·陳禪傳》),豐富了漢地居民的藝術(shù)生活。與此對(duì)應(yīng),我們亦可從《漢書·西域傳下》等文獻(xiàn)中看見西域民族愛重、喜好漢家“鐘鼓”“歌吹”“音樂”,熱心接受并有所傳播的史例。這些記載說明,中原與西域,曾經(jīng)形成了以“音樂”為主題的活躍的文化交流。正如《史記·樂書》所說,“樂者,天地之和也”,“樂和民聲”,“禮樂”可以使得“四海之內(nèi)合敬同愛”。據(jù)《新書·匈奴》記載,賈誼曾經(jīng)提出以“音樂”等方式增強(qiáng)草原民族對(duì)漢文化的認(rèn)同。后來歷史的演進(jìn),說明了漢文化的對(duì)外傳播中,包含中原音樂通過絲綢之路交通通道向西傳播這一方式。
除音樂之外,漢魏上層社會(huì)對(duì)西域“珍香”的追求,通過曹操高陵出土的“香囊”得到了實(shí)證。這一小小的物件,說明了中原社會(huì)生活的許多方面都受到了循絲綢之路而來的遠(yuǎn)國的影響。
《漢代絲綢之路文化史》一書,沒有論及佛教來華。但值得注意的是,無論是經(jīng)過陸路還是海路,佛教西來都是絲綢之路史上重要的文化現(xiàn)象。
四
出土于湖北鄂城的一面漢鏡,銘文可見“宜西北萬里”等字,透露出漢代社會(huì)對(duì)于西北方向的特別關(guān)注。
首先,值得注意的是,這面銅鏡出土自遠(yuǎn)離西域的長江流域。長江流域的出土文物內(nèi)容能涉及“西北”,反映了絲綢之路交通對(duì)當(dāng)時(shí)漢文化風(fēng)貌的全面影響。其次,“宜西北萬里”,體現(xiàn)了時(shí)人對(duì)以“西北”為方向的“萬里”行程持有樂觀的態(tài)度,其展現(xiàn)的英雄主義與進(jìn)取精神是積極的。再次,銅鏡銘文“宜西北萬里”緊接著“富昌長樂”,或許還體現(xiàn)了向西北方向的“萬里”行旅與經(jīng)濟(jì)生活的聯(lián)系。
認(rèn)為邊塞文學(xué)極具英雄主義與進(jìn)取精神的人們,其實(shí)應(yīng)當(dāng)注意,中華民族雄健有為的文化風(fēng)貌,較早地出現(xiàn)在漢鏡銘文的歷史先聲中。而這樣的表現(xiàn),是與絲路交通聯(lián)系在一起的。當(dāng)后世之人回顧漢代博望侯張騫、定遠(yuǎn)侯班超等人的勵(lì)志故事和英雄人生時(shí),也可以體會(huì)到,與絲綢之路交通密切關(guān)聯(lián)的諸多文化現(xiàn)象,對(duì)漢文化起到了充實(shí)和激勵(lì)的作用。
感謝劉進(jìn)寶教授和甘肅教育出版社的美意和辛勞,《漢代絲綢之路文化史》得以列入“中亞與絲路文明研究叢書”面世。然而,這本《漢代絲綢之路文化史》也不能總括從文化史視角考察絲路史的諸多學(xué)術(shù)主題,缺失與遺憾必然難免。我想,不妨把今天的考察心得當(dāng)作日后相關(guān)問題研究的初階,以期繼續(xù)攀登。這樣的態(tài)度,可能是適宜的。
(作者:王子今 來源:光明日?qǐng)?bào))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