嚴謹詩意兼美 守正創新相成
——讀戴偉華《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》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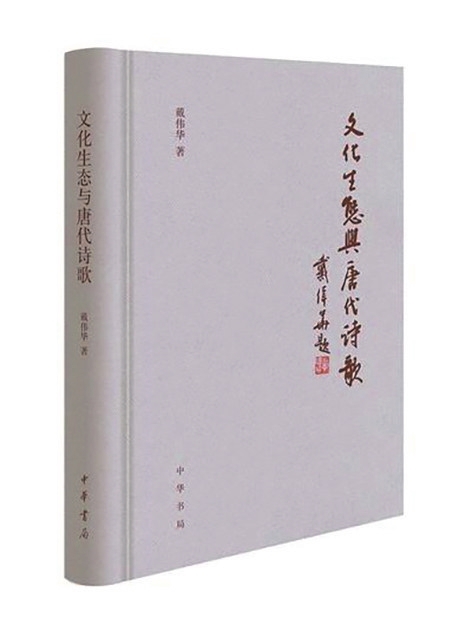
《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》
戴偉華 著
中華書局
戴偉華深耕唐代詩歌與唐代文化研究近40年,以文獻功力深厚、文理分析深微著稱。《唐代幕府與文學》《唐代使府與文學研究》《地域文化與唐代詩歌》(修訂再版為《地域文化與唐詩之路》)等既往著作的意義,不僅在于貢獻出創新性的研究成果,也可作為研究方法的示范。戴偉華秉持“在歷史中理解文學”的研究理念一路走來,他的新著《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》,亦以新的思考推進和深化唐詩的研究。
文化生態可以簡單理解為文化形成與存在的狀態。戴偉華以文化生態視角切入唐人詩歌研究,對相關文學活動、文學現象做出細致精微又宏觀立體的觀照,在突出詩歌主體地位的同時,對詩歌性質更有別出新意的發微。本書各篇章內容彼此獨立,又自成體系,著者實證治學的精神與細讀文本的功力,外化為本書視野廣闊、思理綿密、考論精詳、探索創新的學術格局。
融貫全書的感性與浪漫氣質同樣令人印象深刻。對唐詩數十年如一日的熱愛成就了這部著作,對揚州濃郁的故鄉情懷引發了情思并舉的“能不憶江南”系列研究,對嶺南文人張九齡的持續關注源于生活在廣州的地域文化氛圍。《〈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〉書成用杜工部戲為六絕句韻以詩代序》詩、書并茂的別出心裁,則映照出作者熱愛生活,詩歌和書法兼擅的雅人深致。
新穎多元的研究視角
文化生態是一個處于不斷發展與完善中的動態概念,具備開放包容、涉及面廣等特點,不同的研究目的,會賦予它不同的內涵與外延。戴偉華對詩歌文本的解讀,常因觀察角度的別致而產生創新性的結論。例如,立足宮體詩“自贖”、七言詩“自振”的研究,彰顯出張若虛《春江花月夜》非凡的文學史意義,此已為人所熟知。本書以強、弱勢文化為視角的《與帝京對視的〈春江花月夜〉》篇,則結合初唐南北文化差異與沖突并存的文化生態,從江南文化“自尊”的新角度,闡釋了此詩為何而作的問題,有理有據,耳目一新。
學術研究中,視角、理論、方法是共生互彰的關系。戴偉華很早就關注到文人“才”“遇”錯位及由此引發的文學史書寫問題,并有持之以恒的思考。本書第三章《政治與文學“才”“性”論》不僅對始于孔子的“才性論”做出明晰的闡釋,也集中論析了李白、杜甫、劉禹錫、柳宗元等詩人的命運。以此為例,可知文化生態與文學關系的多元視角兼具學術視野、理論與方法論的多重價值。
敏銳清晰的問題意識
新理論的提出、新視角的選取、新方法的運用,最終目標都是要發現新問題、解決新問題,更好地認識文學及與文學相關的現象,否則便失去從新視角進入文學的意義。
新的研究視角,有助于新問題的提出與解決。面對研究已相當深入的唐人唐詩選本《河岳英靈集》,著者提出“鄉居江南的殷璠是如何獲得入選詩歌的”“《河岳英靈集》的編選意圖是什么”“為何殷璠在《敘》中稱‘開元十五年后,聲律風骨始備矣’”“《河岳英靈集》‘起甲寅’的依據是什么”等一系列問題,經過翔實考論,著者一一予以闡釋。在此過程中,著者閱讀這一選本的態度與路徑,也為與文獻編纂相關的文學、文化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啟示。
戴偉華對詩歌的文化性質及相關問題有敏銳的覺察力。《狀江南》系列研究除了分析李嶠《十二月奉教作》、敦煌《詠廿四氣詩》及文人詩歌《狀江南》不同的文學與文化層級,還特別論及孟浩然《過故人莊》與《詠廿四氣詩》的相類,認為此詩“為探索盛唐文人創作與民間創作相互影響提供了可行性案例分析”。詩歌創作與傳播過程中,文人化與民間化存在互動融通現象,這極有可能成為唐詩研究的一個新學術增長點。
深厚扎實的文獻功力
扎實的文獻工作有助于發現新的學術問題。文學研究中,可信的材料是基礎,對文本的細讀是王道。戴偉華發現有關大歷年間鮑防等人《狀江南》唱和的研究成果中,“狀”的含義一直處于被忽視的狀態,與相關文本的誤寫有關。《全唐詩》題作《狀江南》的組詩,在宋代文獻《古今歲時雜詠》《唐詩紀事》中的詩題為《狀江南十二月每句須一物形狀》。秦瑀為鮑防亦有參與的《柏梁體狀云門山物》唱和所作序文中,有“狀,比也”“義取睹物臨事”的記載。他認為《狀江南》“睹物臨事”“每句須一物形狀”是詩人們集體約定的寫作規范,通行字典亦應據此補上“狀,比也”的義項。由此可見,被明確了的概念可以促進相關研究的深化,而對可信文獻的深入思考,能解決新的學術問題。
以解決問題為旨歸的嚴謹考述,是本書的研究方法,也是研究風格。戴偉華對文獻的精熟掌握與高度敏感,落實到本書的研究中,主要表現在以下兩方面:第一,善于對常見材料進行深度解讀。在政治、律歷與文學關系的視域中,重新審視王灣“海日生殘夜,江春入舊年”被張說書于政事堂的史實時,他闡明這一事件不僅具備引領盛唐氣象的詩學史意義,也表達了政治家們的理想與銳意改革的決心,可稱眼光獨到。第二,重視發掘被人忽視的“隱性”材料,解決了一些長期以來被學術界誤判的問題。“隱性材料”這一概念是著者在《李清照〈武陵春〉詞應作于紹興元年考——兼說“隱性”材料的價值和利用》(2003)一文中正式提出的,這既是他深厚文獻功力的理論化,也是他治學精神具體而微的一個側面。借助《自宣城赴官上京》等“隱性”材料,本書《杜牧詩中的“揚州”不在“江南”》篇糾正了“唐代江南包括揚州”及“《寄揚州韓綽判官》寫于洛陽”這兩個持續長久的誤識。過分依賴數據庫的使用,導致當下的部分學術成果存在以材料掩飾淺陋的弊病,材料堆砌如七寶樓臺,炫人眼目,卻提不出真正有價值的學術問題,也很難看到研究者的精見卓識,可謂得“筌”而忘“魚”。“E考據”的學術環境下,重視“隱性”材料的倡揚與力行,無疑具備匡扶學風的現實意義。
守正創新的治學精神
文學研究的對象是文本與文獻,與之相關的研究可以析為兩重目標與意義,一是把研究對象搞清楚,二是使文本及其研究產生意義。本書守正創新的價值內涵與現實導向也可從這兩方面加以體認。
戴偉華對揚州學派考證精詳、敢于創新的學術傳統有自覺的歸依與發揚,他認為學術創新不是刻意獵奇,而是在具體作品、現象的論述中探索一般性的知識結構與理論體系,以發現文本新的意義和價值。本書具體創新的類型有二:一是對自己既往研究的補充與完善,二是源于多元視角與文本細讀而形成的新觀點。前者以杜甫《飲中八仙歌》的重新闡釋為例。他認為此詩應當系乾元元年杜甫居官左拾遺時。杜甫意在通過詩歌創作,與符合自己理想的“飲中八仙”神交,并借此構建自己的盛世記憶。因為此詩,“飲中八仙”也成為長安乃至大唐盛世風流的文化符號,故不宜做過多政治化的解讀。
將嚴謹的學術研究與對當下的深切關懷融為一體,是戴偉華始終如一的學人風范。雖然研究對象是歷史文化場景中具體的事物與現象,但對現實的自覺關注已深融于著者的意識。在指出《狀江南》別樣格調與開拓意義的同時,他特意強調說:“現在各地都在做地方文化梳理、挖掘,《狀江南》唱和組詩藝術的特殊性和創新性,在江南文化研究中應被充分重視。”又如,這種當代意識也體現在對岑參邊塞詩以詩證史價值的重審,他認為這些側重西域的詩歌,“對于今日新疆而言以詩證史是唯一性的”。
作為新的文化生命體的中華民族現代文明,是“革故鼎新、輝光日新”的文明,是熔鑄了優秀傳統文化的現代文明。如果說作為本書研究對象的《早朝大明宮》《飲中八仙歌》與大歷年間浙東詩人們的《憶長安》,意在承續對盛世大唐的文化記憶,那么,《文化生態與唐代詩歌》的深層寄托便是戴偉華傳承文化的責任感。唐詩的創作只是在時空上遠去,唐詩的文化魅力卻可以借由讀者的情感共鳴、學者的精深研究生生不息。
(作者:陳彝秋 來源:《光明日報》)
下一篇:沒有了

